![]()
![]()
![]()
初六,立春,有人提醒要早起,因为一年之计在于春。然而我还是睡了个自然醒。也有人提醒我,立春这一天,生肖蛇、虎、候、猪的必须躲春。最好关闭门窗,安静独处。甚至要拉上窗帘,禁语。这种事情不提醒还好,若是提醒了却不遵守,总是心里不踏实。
我生肖属虎,照古人的风俗,也是要躲春的。但是早在几天前,我已经答应了高阁老师的邀请,今天下午去李可染画院,与可染之子李庚老师一起喝茶吃饭。一早我与高阁聊起躲春之事,她笑着说:“以你的正心正念与强大的气场,一切邪怪都不敢靠近你。”我心想,这倒是说得有道理,比古人躲春一说更接近宇宙的真理。再说,李庚老师也属虎。两只老虎见面,岂不虎虎生威?我当下释然。
我在一年多前曾参加了李庚老师的一个画展,并写过一篇文章。自那一别,直到今天才又再次相见。相比上次见面,他似乎又苍老了一些,但是穿着米色夹克的他看起来比上次更加亲切而慈祥。久别重逢,彼此欢喜,坐下后,一番畅聊。他与我聊起李政道先生的艺术与科学观,并试图从多个维度进行深入探讨。同时也提到他父亲李可染先生作为中国艺术界的代表,当年与李政道先生见面时的对话,在他这里一直是一个谜。他说他有时会发呆,那个时候,他总是会想当年他父亲和李政道先生到底是如何探讨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微妙关系的?他针对这个问题,聊了许多。
![]()
![]()
那一刻,仿佛他在艺术家之外,也是一个科学家。因为他试图去弄清楚的其实早已经不是一个艺术的课题,而是一个科学的课题。也或许,艺术与科学原本就是一个硬币的一体两面,或者是多维宇宙中不同的面,也或者如同太极图中阴阳和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如科学家的瞳孔与艺术家的视网膜,原是同一种捕捉宇宙震颤的感光元件。科学与艺术作为硬币的两面,这枚被文明之手反复抛掷的银币,正面刻着爱因斯坦质能方程的微分符号,背面却晕染着八大山人的枯荷残叶。当物理学家在超弦理论中推演十维时空的褶皱时,李可染的重墨水彩正在宣纸上诗意流淌,瀑布飞流直下,飞鸟跃然纸上……那些被称作“创造力”的量子隧穿效应,既能让李政道写下“宇称不守恒定律”,也能让李可染的黑白水墨刺破宣纸的维度。
是啊,人类文明史不过是部寻找对称破缺的美学手稿。商周的青铜饕餮吞食着夸克禁闭的隐喻,敦煌星图与哈勃望远镜共享着螺旋星系的悬臂。当丁肇中在反物质海洋垂钓时,黄宾虹的夜山图正渗出暗物质的墨色。或许真如李政道所言:科学家攀爬的雪山与艺术家潜游的深海,终将在海平面下六千米处的莫霍面相遇——那里沸腾着地幔的岩浆,也结晶着《溪山行旅图》的岩脉。
我看李庚老师在这个问题中久久没有出来,我知道他或许一直没有找到他想要的答案。于是我善意地提醒道:“或许站在上帝的视角来审视这个问题,就会看到真相。”
是啊,若只是站在人类的视角探讨这个问题,都是片面的。每一个存在,都是一个独立的宇宙,然而又都是整体宇宙中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
![]()
![]()
![]()
正如山有千面,水有万声,血脉中的墨色亦是另一种不息的潮涌。正如李庚站在父亲李可染的巨峰之下,却不曾将自己缩成仰望的影子。他执笔时,宣纸上浮动的不仅是松涛云海,更有一段穿越时空的对话——父辈的苍黑山水在他腕底化作流动的星河,东方水墨与西方抽象在某个晨昏交割的刹那,撞出漫天磷火。
他幼时伏在案边,看父亲用羊毫蘸取宿墨,层层积染出混沌初开的天地。那些墨块里藏着的不是技法,而是李可染对着黄山云雾吞吐的呼吸。少年李庚却从父亲严谨的笔法中,听见了贝多芬的赋格曲。七十年代,他负笈东瀛,并蜚声海外。这个下午,我有幸听他娓娓道来,给我讲述他在日本留学时的那些故事!他曾被教语言学的女老师当作智障,最终他却成为当年那个班上唯一一位收到日本著名学府研究生入学通知书的人。他学不好日语,却征服了日本著名大学的校长。对他说,我们这个学校如果你能看得上的话,欢迎你随时来校就读。在他刚读完大一时又对他说,你不用学习了,就直接成为我们学校的教授吧!就这样,他成为了那个学校最年轻的教授。
他的画作征服了日本人,因为他在京都古寺的枯山水里,发现了八大山人的孤禽与蒙德里安的色块原是同一种精神的褶皱。当我观望着书房的墙壁上那丈八的大幅山水,我看到的却不仅仅是山水,而是解构山水的史诗。当人们期待他能重现他父亲的《万山红遍》的恢弘时,他却把朱砂碾成齑粉,泼洒成《马勒交响曲》的炽热光谱。浓墨不再是山峦的轮廓,而是勃拉姆斯低音部里涌动的暗流;留白也不再是云气的婉转,化作勋伯格无调性乐章中突然的静默。那些线条与色块,细看竟是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散落的基因,在抽象表现主义的土壤里长出新的年轮。
有人指摘他背离了“李家山水”的正脉,却不知他书房里常年悬挂着父亲手书的《东方既白》。这四字于他,不是暮色中的挽歌,而是破晓前的实验场。他把敦煌壁画的飞天体态揉进康定斯基的几何狂想,让范宽《溪山行旅图》的巍峨在塔皮埃斯的物质绘画中重生。水墨与油彩的媾和,不是简单的混血,而是将两种文明DNA螺旋式纠缠,孕生出带着金属光泽的东方玄学。
![]()
![]()
![]()
当他痴迷于各样的雪峰,却在写生册页里画出了终南山炼丹炉中的紫烟。恍惚看见李可染笔下漓江的倒影,正从马蒂斯的色域中缓缓升起。这何尝不是最深的传承?当他在卢浮宫临摹德拉克洛瓦时,狼毫扫过的每一道血痕里,都蜷伏着石涛“一画论”的魂魄。
看着他的满头银发以及微微颤抖的手,我感叹岁月的无情,将一个曾经调皮捣蛋的少年催促成了这样一位开始回忆往昔的老人。然而我也从中感受到他天真的本色,他其实一直渴望着自己能像墨色挣脱纸纤维的桎梏那般,挣脱某些束缚。所以他说,当年在国外留学时,他从不告诉同学们,他的父亲叫李可染。
然而无论他说与不说,他一生都逃脱不了他与李可染之间的关系。他想要逃脱的,正是无数人渴望拥有的。他的母亲邹佩珠先生亦是一位艺术大家,是中国当代最早的女雕塑家。说来,早在十三年前的2012年,佩珠先生还曾参加过我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新书发布会。
当李庚老师得知还有这样的渊源,他让我坐到他母亲曾经坐过的那个位子上,我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
![]()
![]()
![]()
![]()
![]()
这一天,要数我的收获最多。在李可染画院秘书长李九红先生的陪同下,我们还参观了李可染博物馆,里面按着先生当年艺术、生活的轨迹做了布置,还有许多先生当年的收藏与珍藏。我最是喜欢先生那些黑白素描的手稿,虽然画幅很小,却令人的心一下就静了。
作为李可染画院数字与创新艺术研究院院长的九红先生赠送了三幅他亲笔签名的数字作品。另外,我还从李庚院长的手中接过了他的一幅花鸟原创。
临别时,李庚院长对我说:“今天很开心,你的思维很活跃,思想很丰富,你要常来,我还有很多话题想与你交流!“
是啊,若不是为要躲春,又心疼院长的劳累,感觉还有千言万语要聊,下午的对话仿佛才刚刚开了个头……
沈思源于2025年2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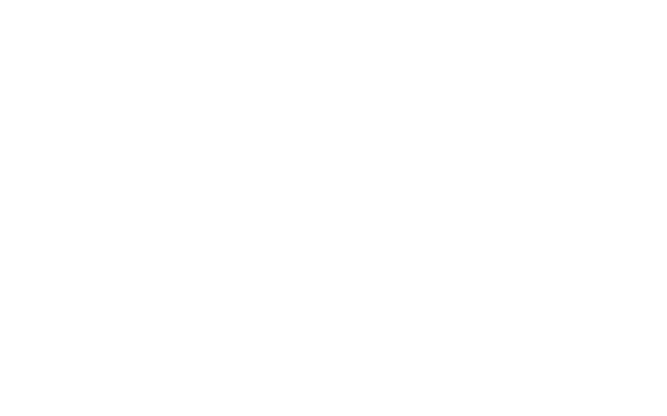

 2元
2元

 5元
5元

 10元
10元

 50元
50元





 举报
举报





 默认
默认 时光
时光 水墨
水墨 冬季
冬季 美好
美好 春节
春节 岁月
岁月 星空
星空 前行
前行 回忆
回忆
































